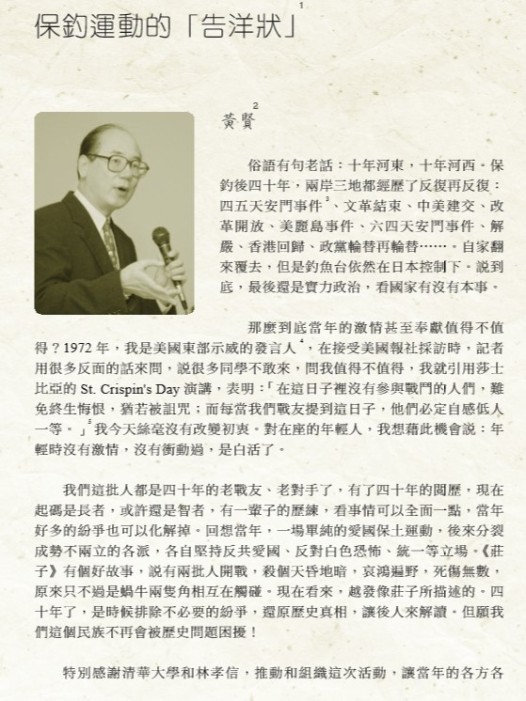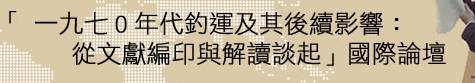
Shortlink 鏈接本頁: http://wp.me/p28B6z-7w
Full text 全文:保釣運動的告洋狀
— 載于《啓蒙 狂飆 反思 – 保釣運動四十年》(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編)100-109頁。
保釣運動的「告洋狀」
黃 賢
俗語有句老話: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保釣後40年,兩岸三地都經歷了反復再反復:45天安門事件、文革結束、中美建交、改革開放、美麗島事件、64天安門事件、解嚴、香港回歸、政黨輪替再輪替… …。自家翻來覆去,但是釣魚台依然在日本控制下。說到底,最後還是實力政治,看國家有沒有本事。
那麼到底當年的激情甚至奉獻值得不值得?1972年,我是美國東部示威的發言人(年表裡頭好像沒有提到這個示威),在接受美國報社採訪時,記者用很多反面的話來問,說很多同學不敢來,問我值得不值得,我就引用莎士比亞的St. Crispin’s Day演講,表明:「在這日子裡沒有參與戰鬥的人們,難免終生悔恨,猶若被詛咒;而每當我們戰友提到這日子,他們必定自感低人一等。」我今天絲毫沒有改變初衷。對在座的年輕人,我想籍此機會說:年輕時沒有激情,沒有衝動過,是白活了。
我們這批人都是四十年的老戰友、老對手了,有了四十年的閱歷,現在起碼是長者,或許還是智者,有一輩子的練歷,看事情可以全面一點,當年好多的紛爭也可以化解掉。回想當年,一場單純的愛國保土運動,後來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各派,各自堅持反共愛國、反對白色恐怖、統一等立場。《莊子》有個好故事,說有兩批人開戰,殺個天昏地暗,哀鴻遍野,死傷無數,原來只不過是蝸牛兩隻角相互在觸碰。現在看來,越發像莊子所描述的。40年了,是時候排除不必要的紛爭,還原歷史真相,讓後人來解讀。但願我們這個民族不再會被歷史問題困擾!
特別感謝清華大學和林孝信,推動和組織這次活動,讓當年的各方各派,不分左中右,是戰友、朋友還是死對頭,可以相聚一堂,重敘往事,釐清歷史,暢所欲言。
主辦單位原本找我講的題目是介紹我經手和收藏的1970到1978年間的保釣、統運和支援島內民主運動的有關資料。我是律師訓練,破爛的紙條都會收起來。原本有十多箱的資料,當時在幾個地方分頭保管,但是今年初為了準備這次會議去找的時候,才發現全部失蹤了,只剩下一些印刷品,所有手稿全部不見了,大概是因為有很多敏感的資料。由此想起,要提高警惕,畢竟現在還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干擾。建議兩岸收集到的所有資料,都應及時掃描,按OCLC編制索引,上載到IPL網絡世界,保存在虛擬雲端。
想到兩個替代題目。第一個是兩地官方的影響,包括其錯誤指導思想,如何誤導了海外的學生,影響了局勢。對台灣方面的情況我有點了解。台灣末任駐聯合國大使劉鍇是我的親戚,我到美國後拜訪他,有一次提到保釣,他便替我調閱資料,也請陸以正幫我找資料。對大陸方面則知道更多。他們對台灣、海外的認識,有很多局限性,很多錯誤的想法。錯到什麼地步呢?看看1972尼克森、周恩來祕密會談,周恩來是很有信心,認為七○年代就能統一。這是錯得不能再錯的。到了八○年代鄧小平最重要的講話「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三大任務之一居然就是八○年代要統一!這些徹底錯誤的結論源於認識不足和情報嚴重失誤,還不多不少影響了海外的運動。但是這個問題太敏感了,還不方便講,況且目前解密的資料還不夠,就留給日後的會議吧!
另一個選擇就是「告洋狀」。題目有點偏門,還稍微過分煽情一點,所以用引號。選這個題目的目的,是強調要把整個運動的空間拉開一些,走出漢語和華人這個圈子,看看去做「外國人」的工作。我在這方面花了很多工夫,不是為了別的,而是1970年我從香港到美國時不會講國語,所以就成了啞巴不能工作,只好多發揮英語能力。因我直接參與較多,好掌握分寸,顧慮相對較少,就選這個題目。
收集「告洋狀」文獻的意義:
- 從保存保釣文獻的角度:必須走出漢語圈才算全面。「告洋狀」是一種特定的文體,是用外語撰寫或形成、爭取非華人支持的文獻,如向美國人發傳單、在《紐約時報》登廣告,向外國政府發公開信等等。釣魚台問題涉及日本和美國,活動最多最持續的地點應是美國、既有保釣人士形成的文獻(如各種外語文章、傳單、音像資料),也有官方的資料(譬如說各地政府機構監視保釣分子的資料),還有各地民間支持者的資料。要強調,大塊文章以外,其他形式的各種文字音像資料也同樣有解讀事件的功能。
- 從解讀的角度,可以探討實效的問題:究竟能不能起作用,究竟有沒有起作用?有什麼經驗供日後參考?如何配合天時地利人和去「告洋狀」?如何按不同對象去實施?目前日本立場依然堅定,要不要「告東洋狀」?
- 從倫理角度:有沒有道德風險?為什麼要「告洋狀」?贊成就是媚外?反對就是民粹?怎樣界定,在什麼情況下絕對可以或不可以「告洋狀」?
謹此從個人直接參與的角度看看有那些方面的「告洋狀」文獻可以收集(解讀則有待後人)。
我在美國參與保釣運動,是從1970運動開始,到1978年中回香港前。主要活動在美國東部和中西部,以波士頓、芝加哥為中心。這期間保釣運動大體上可分為幾個方面或階段:保衛國土、統運、支援島內民主運動。而運動的每一方面或階段,都涉及三個不同的目標和對象:喚起國民、爭取美國民眾、影響美國當局。針對後二者的活動,都可算是「告洋狀」。
這期間,我有幸和一大批戰友並肩活動。他們主要來自台港,也有華僑。還有一批紅黃藍白黑的進步人士,他們既配合華人的活動,支持保釣,又帶領我參與遠方的民族解放運動、獨立運動,大大開拓視野,融入當年席捲全球的潮流。下面講的,是群策群力的成果。
1970年,釣魚台被佔領的消息傳到波士頓。我寫了一篇,也可能是第一篇用英語寫的有關釣魚台法律問題的文章:Tiaoyutai: A Legal Analysis,方便美國人了解問題。現在這個小冊子我自己都沒有了。1970年年底紐約示威,黃色廣告板的英語說明就是從那裡摘錄出來的,圖書館這次有展出那個廣告。早上有人說老林辦《科學月刊》太忙,所以書讀不成,這個就是香港跟台灣的差別。香港人就會走捷徑,我想的就是為什麼我不能把這篇文章當成課程的作業呢?當時我在哈佛為自己設計了一個獨立研究課程(這本身就是個捷徑),跟約瑟夫•奈教授,也就是「軟實力」的那位。我就把這個作為作業交給他。他在報告上批示:「我終於了解這個問題了;你比我更了解」。哈佛每學期才四門課,這也算一門了!所以「學」和「戰」不是對立的!很遺憾奈教授的批示也不見了。
1970年底的遊行示威,是幾十年來華人在美國的第一次,引起美國媒體的注意。PBS公用電視台(觀眾多是知識分子)還找我上電視辯論釣魚台問題和日本軍國主義,對手是Edwin Reischauer教授,就是前美國駐日本大使。但我一點都不怕他,因為當年我報讀哈佛,是他特別從美國飛到香港去面試的。面試時,他無意講錯一句話,立刻被我揪住。他是知名人士,但我敢挑出他的毛病,立刻就把我錄取。我的中學辦校140年了,孫中山先生是校友,現在我們學校招生的時候,也會設計在面試時老師故意講點錯的,哪個小孩說出來就立刻錄取。這樣才能延續反叛的基因。
但到了1972年,第一次打著五星紅旗在華盛頓示威,形勢已大大改變。這是一個很傷心的結果。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總統已去過北京,所以沒有新意了。連有些來採訪的記者都以為香港在日本,不知道台灣在哪裡。而釣魚台的韋氏拼音有個重音符號,在美國人看起來就是外國的東西,所以並不理會。在一個天天都有遊行示威的首府,沒有新意就不受注意。結果沒有一個報紙報導。連華盛頓本地的報紙都沒有,這個我們就要深刻反省。
從反省到覺悟,怎麼辦?就做了幾方面工作,首先是要融入美國社會:任何不是植根於本土,而是在別國的運動,一定要結合當地的老百姓。所以就成立「全美美中人民友好協會」,會旨是我寫的,這個協會多年來在全美各地做了好多打頭陣的工作。在波士頓還辦了好幾件事,包括開辦「康橋書屋」,賣中英文刊物,介紹大陸,也是鄉土文學書籍以及《大學雜誌》的主要銷售點(還擔當了其他國家進步人士的秘密聯絡點!)。我日前在箱底僅存的資料中找到兩份康橋書屋的鄉土文學目錄,轉贈兩岸各一份。
還成立了一個Asian Film Society,是美國正式註冊的非營利組織,不是為了免稅,而是因為有了這個執照之後,寄傳單幾乎是免費的。這個組織的工作是放映有關大陸的電影,早期還肩負製作英語字幕的工作。各位如果當年看過大陸的紀錄片、故事片,幾乎所有的英文字幕都是由這個小班底做的。國內有電影要拿到美國放映前,會先把旁述或對白送到波士頓,全部翻譯成英語。為什麼要翻成英語呢?因為如果只用漢語放映,來看的都是自己人,僅僅能鞏固基本群眾,好像神父向教徒傳教一樣,圈子會越走越窄。我們是要走出教堂,融入社會。
今天多次提到當年在台北的香港僑生不怕死,釣運早期靠他們去打頭陣。在美國何嘗不是。但是也會面對後繼無力的情況。因此辦了一份《港外線》刊物,鼓勵香港同學多關心時事國事,甚至參與海外運動。
1976年是美國大選年,美中關係必定是議題。一方面,季辛吉礙於選情,又想藉此操弄他的美蘇中三角關係,反對福特總統推動美中建交;而另一方面卡特的選戰,大打人權牌,強調盟友關係等等,更不傾向於建交。由尼克森自1971年開啟的美中關係正常化進程,似乎要放緩。
然而,當年的國民黨及其外圍組織的所作所為,有助扭轉形勢。1976年一連串的「事件」,處處損害了美國的核心價值。「告洋狀」緊扣這個因素,起了正面作用,有利促進美中建交。
首先是「導彈事件」。1976年一月,國民黨被揭發派遣15名有軍方背景的學生,到麻省理工學院(MIT)以學習民航導航科技名義,違反美國規定,企圖掌握精密導彈制航技術。二月六日,留學生以「告洋狀」形式,在MIT舉辦了一場聲討會,披露此事,引起校方和美國政府注意。經美國有關部門調查後,該項目被中止(詳見當年的《七十年代》)。
繼而是「監視學生事件」。在上述聲討會上,國民黨駐波士頓領事館的一名官員和一名有海軍官銜的研究生不斷拍攝與會人士,是典型的恐嚇、打小報告手法,引起轟動。國民黨派遣特務、職業學生監視美國高校的台灣同學,被廣泛報導。MIT校長決定正式調查此事。同學們排山倒海地「告洋狀」,提供資料;起碼十所大學的報刊作了專題報導。最後,MIT發表了一份35頁的報告,認為有足夠理由要徹底調查國民黨監視留學生的指控。報告還建議美國全國留學生指導員協會進行一次全國性的調查,了解外國政府監視其留美學生的狀況,更要求國務院介入,訓喻各國駐美使館終止在校內外收集留學生的情報。這是首次由權威機構認定國民黨監視學生應確有其事。
接踵發生的是「特務會議事件」。進行監視留學生的國民黨外圍組織的各地小組負責人在波士頓開會,地點是郊區的一個小飯店。我們掌握到開會的時間、地點,便假借送禮的名義,需要他們的名單,飯店就把名單給我們了。拿到名單後,「留中不發」,不為短期宣傳效果而將其公開,而是發給各地,讓各地掌握情況,敵明我暗,作出應對。
十一月底,美國大選後不到兩週,島內就發生了「陳明忠事件」。陳明忠被秘密判處死刑,消息經國際友人傳到美國後不到幾小時,就能迅速組織起來,發動營救運動,兩天內就在《紐約時報》登出標題為「反對政治迫害、立即釋放陳明忠」的廣告。這個廣告是後來許多廣告和公開信的開始,這次圖書館也有展出。日後還有「淡江事件」,「郭雨新事件」和屢禁像《新生代》、《夏潮》等民間刊物的各種「事件」;這次會議有專題報告,茲不贅。
這裡要特別提出的是廣告的聯署人。很多人(特別是華人)只注意到有多少人得過諾貝爾獎,但這只是一方面。這些諾貝爾獎得主,以其權威性,能觸動讀者的腦袋。但光是觸動腦袋並不夠,還要抓住讀者的靈魂。而要抓住美國人的靈魂,一定要抓住他們當時佩服的人,即時代的符號。因此看這些廣告和公開信,就要注意我們把反越戰的英雄幾乎都請到,因為當年,反越戰已經成為美國的主流。我們說服美國的「良心符號」來聯署這些廣告,可以說是正義之師,得道多助。順便一提的是,當年大陸曾錯誤判斷支援島內民主運動,起了極壞的影響,到了1978年底才初步開始糾正,後遺症延續至今。
1977年一月底,卡特政府正式上任。一月三十日,我們就來了一次最高層次的「告洋狀」,向新當選的國會發了「公開信」,並附上1976年各種「事件」的詳細資料,共38頁(我只找到一份這個資料)。
因為做了這些工作,就帶來一些突破。美國國會關於台灣的聽證會,我們跟國際特赦以及美國參、眾兩院有關委員會密切配合。合作到什麼地步呢?講者的稿我們都可以修改,國會議員的發言稿我們能修改,甚至代為操筆。我估計我的東西不見了,有可能和這有關。聽證會的主人、客人、所有人的稿我們都有機會參與整理。但那是會精神分裂的,因為不能改寫成一個模樣,要保持各自的風味,各有其空間可以讓他發揮,但又不至於出格,這樣才能持續發展。令人欣慰的是,當年和我們接觸的美國議員、官員,好幾位後來都升到高位,包括主管東亞事務和國家安全事務。
有了這個合作基礎,就能建立關係,把國民黨這些違反人權、損害盟友的行為的詳細資料(為加強份量,還整理了其他如伊朗沙皇和韓國朴正熙的同類罪行),通過有關人員直達行政機構最高層,化解了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高層對美中建交的倫理顧慮。往後就是歷史了。
「告洋狀」究竟有沒有用?我相信有機會參與的人(不管現在的政治取向如何),當年都熱情投入,都感覺良好,自拍胸口當然說有用。而當年得到的反饋,也確實說有用。可是幾十年後,現在成了長者,我每年一月都要重新看一次尼克森、季辛吉跟周恩來秘密談話的記錄。為什麼每年都要看呢?因為每年都會多解密一點。到今年的版本,尚未解密的就剩下談到日本的一段,不是尼克森罵日本(前幾年已解密),而是周恩來跟尼克森談到有關日本的一些實質問題。是不是有關釣魚台呢?明年或許能揭曉。看完他們的講話,難免悟出一個簡單道理:一切都是大勢所趨。至於當年我們做的這一切究竟有沒有起作用,唯有留待後人去考證;但我們能做的都盡力去做了,倒也覺得挺滿足,沒有白活!
有沒有道德風險?我有我的看法,但40年後也不在乎了;留給後人去解讀罷!
(2009. 05. 02在台灣清華大學舉辦的「一九七○年代保釣運動文獻之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上的發言)
Full text 全文:保釣運動的告洋狀
— 載于《啓蒙 狂飆 反思 – 保釣運動四十年》(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編)100-109頁。
Back to Menu 目錄